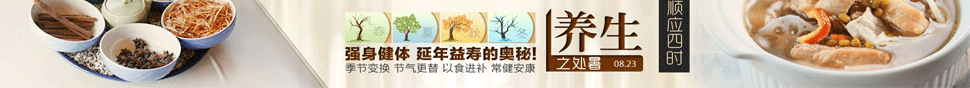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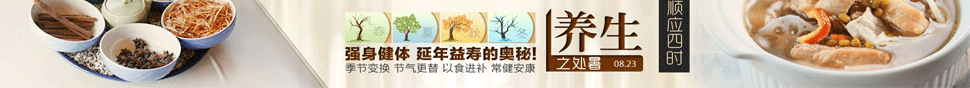
岑巩县思州古城水码头记忆
文丨张维军
来源丨黔东南日报
正在修复建设的思州古城水码头
秋来天凉,行走在岑巩县思州古城的水码头,河风撩人。龙江河与小河环绕古城奔流而出,交会后溜过南岳古寺下一面绝壁,画出一道“S”形的大湾,将一座千年古城,先划成三个半岛,再划出一方八卦太极,人称“水舞太极”。山环水绕的思州古城,是雄奇的,卓异的,令人叹为观止。
傍晚的思州古城
龙江河悠悠的碧水上,只见鹭影翩跹,它们带着仙气的白色倩影,仿佛来自远古的信使。鹭群低低地在水上翻飞,嬉戏,不时发出悠远的鸣叫,催人心底里生起无限深远的旷古幽情。
眼前的这座古城,最早可以追溯到隋代的清江。当时,地方叫清江郡,这条河就叫清江,河滨的城叫清江城,那城是个什么样子,已经无从查考了。
隋朝开皇二年(年),田氏先人田宗显,为朝廷立功,被授予黔中太守。他的四世孙田克昌修筑了思州城(今沿河县),田氏安土占籍,恩威结服少数民族,掌管一方军政大事。唐高宗时,授田克昌为义军兵马使,思州于是成为田家世代领地。田氏子孙世袭土司职,掌管思州八百年天下。清江一带也属于田氏思州的管辖范围。
大唐盛世,王化之风吹来,清江河上飘来了帆影,思州境地鸿蒙开化。此时,佛教开始传入思州,通慧禅师在鳌山上建寺传播佛教,开辟民间寺庙教育,将中原文化的火种播撒在思州大地。此时清江城畔出产的一种黛黑而又金光闪烁的金星石,已在当地生产为石砚销往湖广及中原一带。当时清江一带因偏远荒凉而被称为蛮溪,金星石砚被称为蛮溪砚,竟名盛一时,成为中国古代的“八大名砚”之一。
通慧禅师以高超的民间医术奉命进京为唐玄宗治好了疟疾,他随身带去的思州茶叶,以其优良的品质而被茶圣陆羽载入了《茶经》。这两桩事件载入史册,成为思州后人津津乐道的千古佳话。通慧当时是否将蛮溪砚带去长安,却不得而知,但蛮溪砚名起于汉,产销于唐,确是砚史记载的事实。
龙江河畔搁浅的渔船
元朝至元时期,清江河畔清江城发生了历史巨变,打破了千年的闭塞,迎来了辉煌的发展时期。为了强力开疆拓土、平夷抚蛮、连接外域,有效掌控大西南,促进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,中央王朝开辟湘黔滇驿道,打通了西南连通中原朝廷及外域的大动脉。
此时雄踞西南的田氏大土司,审时度势,借此机会占据天时地利,抢夺地盘,发展壮大势力。田氏将自己在凤冈的土司政权中心迁移到靠近湘黔大道边的清江城,依据得天独厚的水陆交通便利条件,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得到迅猛发展,土司势力迅速膨胀起来。此时,田氏土司政权如日中天,占据了黔东北大部和湖南部分土地,还有飞地在广西及四川境内,统辖了相当于今天贵州省三分之二的地区面积,人口上千万,拥有庞大的土司军队,成为雄霸西南的一个“小王国”。田氏土司对群众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,俨然就是“土皇帝”。
元朝末年,田氏土司内讧,土司政权一分为二,分为思州和思南两宣慰司,司治分别在今岑巩和思南,清江城仍是思州田氏大房统治的土司政权中心。
朱元璋建立明朝,两田氏土司归顺朝廷。明永乐年间,思州、思南土司为争夺汞矿而发动“沙坑”血战,不听朝廷劝阻,永乐皇帝朱棣亲派镇远侯顾成率五万大军平乱,一举荡平思州、思南两大田氏土司势力,并趁机在思州、思南实行改土归流,分其地为八府四州,设贵州布政司予以统辖。田氏土司灭亡,从此,贵州成为内地,纳入中央管辖。
从清江城到思州宣慰司城,到思州府城,再到岑巩县城,每一次变迁都是一次巨大历史震荡的裂变,每一次裂变,都是一次唤醒,都是一次振兴,都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历史文明的演变进程。
思州开府之后,清江的名字变成了洒溪,沿着这条黄金水道,中原文明便名正言顺地涌来,坐镇这片江山,教化这片土地。第一任思州知府崔彦俊将思州宣慰司土城改造成了土石结合的府城。后历经战火、洪水等人祸天灾损坏,历任知府数次修复扩建,逐步形成了一座除了有官署,还有城墙、城门、文庙、书院、民居及其它楼堂馆所等功能完备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,思州之地逐渐走上了与全国步调一致的全面发展的正轨。
民国二年(年),思州府更名为思县。民国十九年(年),思县更名为岑巩县。解放后,为修建龙江河东方红大桥,拆古城城墙石料建桥,又经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的严重破坏,思州古城彻底被毁,只余文笔塔、观音阁、禹王宫等零星建筑。年,岑巩县城从思旸古城南移搬迁到新兴村,思州古城成为了思旸镇政府所在地。
绕城而过的清江,也经历了沧桑巨变。在明清时期清江被改名为洒溪,民国时改名为思州河,解放后,又改名为龙江河。随着现代公路的快速发展,岑巩县境内已经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综合性交通运输网络,彻底取代了水运交通。龙江河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,而成了现代人文化旅游观光的一道美景。
显然,龙江河是岑巩的母亲河。它在玉屏自治县境与氵舞阳河交会流入沅江、庭湖,进入长江。龙江河蜿蜒百里,温柔曲折,中和静谧,大美成趣。两岸山清水秀、田畴相连、村庄错落、民风旖旎,形成百里画廊景致。
龙江河系沅江支流,通达长江水系,是古代中央王朝进入大西南的重要水上通道,是思州文明的血脉。有史料记载,龙江河于唐代行舟楫,元明至清代疏理河道始通航运,10余吨木质商船可在河面畅行无阻,官商船只往来穿梭,船业运输兴旺发达。思州商业发达,龙江河功不可没。
元朝至明代,思州宣慰司、思州府在平溪(玉屏)开创水陆驿,专司军运,主要运送兵丁、军饷和粮草。
明代,思州府东门外的洒溪河滩,停泊着众多官船。清雍正年间,为将官府、商旅、物资运输湖广,在东门口建水码头一座,可泊木船余只。
清顺治十五年(),军旅粮饷由沅江经洒溪入思州府。清康熙《贵州通志》载:“思州颇通商旅,称著庶焉。”清代中叶,洒溪木排、竹筏、木船逐渐增长。清末,洒溪河道经过数次梳理,河面的木材、油桐、茶叶、药材由龙颈坳、罗家山、思州府城、玉屏通过这些水上工具可运达沅江,然后运回百货、布匹。
由于官商航运频繁,思州境内陆续修建了大量码头、水埠和渡口。可以想象那时的洒溪两岸是一片多么热闹繁忙的景象。
在老船工的记忆里,当时龙江河两岸纤道密织,拉纤喊号的纤夫成千上万。两岸渡口星罗棋布,如洒溪渡、天堂渡、注溪渡、龙(颈)坳渡、平溪渡等大小名渡就有好几十个。
在改土归流、土流并治的明清时期,随着官员、士兵、商旅和移民登陆上岸,古城、屯堡、寺庙、会馆、汉寨等具有中原和江南特色的建筑相继出现,军事、宗教、商业等各种文化也随之滚滚而来。
在思州,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与土著边蛮风情经过长期激烈碰撞与交流融会,逐步形成多元、中和的思州文化。如今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各种习俗,徽派建筑、江南民居交错融合于当地苗乡侗寨的现象,都是这种多民族迁徙融合的历史见证。
思州古城与龙江河畔水码头,早已消逝在历史的烟尘深处。龙江河上,除了千年飞舞的鹭影,悠闲的木舟,再无纤夫成群的背影、翻江的号歌和熙来攘往的船影。许多岑巩人已经无从知道发生在思州古城和水码头上的思州故事。
不明来路,如何知道归途?人的寻根意识是刻骨铭心的,看到为政者一片苦心痴情,发起重建古城及其水码头的行动,岑巩人一片释怀欢欣,打从心底里舒服。你看,思州古城与水码头的魅影,带着沧桑古朴,黝黑厚重,仿佛沉重的铅梦一般,稳稳地倒映在龙江河的水波里,永不会再消逝。漫步走过水码头的岑巩人,怀着敬仰与欢欣,试图掬一捧龙江水,带回那昨日重现的美丽。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

